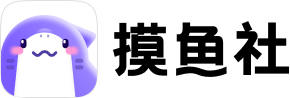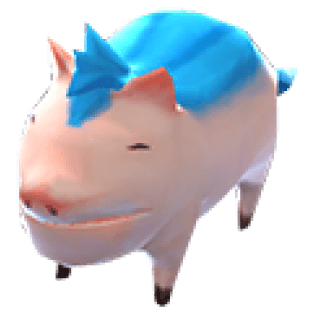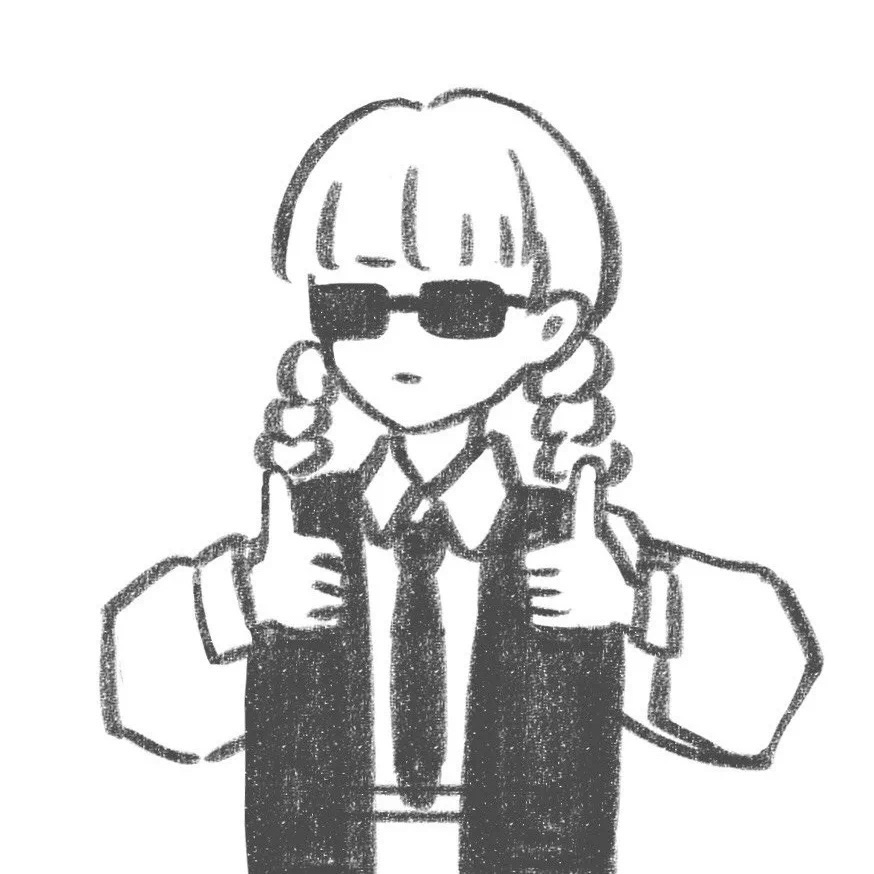“一间屋子一妇人,一生只等一个人,我永远在孤湖等你回来...”
——题记

“这里是拉鲁火山,我出生的地方...我这辈子没有愧对过什么,我没有对不起我的国家,我没有对不起信任我的同伴,唯独,我愧对我的母亲...我...也只是个孩子...”
估算着,大概五十年前,这里有一户人家,很普通,并不奇怪——即使是在拉鲁火山这样的地区,由于其南北有着巨大的温差,仍旧能依靠着旅游业和畜牧业有着不错的发展,而他也是这里的一名普通的居民。
他的父亲是一名军人,在他只有两三岁的时候,父亲便离开了家,去参加了星之塔的战役。但很不幸,在星之塔的征途上光荣了,带着显赫的战功,荣归故里,但却未能马革裹尸还。他父亲的战友,带回来了为数不多的遗物,一把军刀,这是他父亲身前最爱的一把刀,每次出征前都被擦的锃亮,刀尾绑着一块红布,但原本是白色的...一枚弹壳,不知是他父亲开过最后一枪的弹壳,亦或是被敌人打中后留下的弹壳...一块徽章,这个是他父亲参军后,所获得的第一个二等功徽章,他在一次战役中,拯救了一个班的人...最后便是一块布,一块写着他父亲名字的布,每个军人都会在外套内衬上写着自己的名字,以免因为在战斗中因为炮弹残片或者子弹击中面部而无法辨认尸体...
...
这年他23岁,他也走上了父亲的路,成为了一名军人。临行前夜,他的母亲,哭成了泪人,他也想哭,但不能,他知道有国才有家,母亲也知道,但是他是她唯一的孩子,即便大道理再多,母亲也舍不得她的孩子去往一个生死未卜的地方。他也知道,如果他离开,母亲将会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这天半夜,母亲前往他父亲的墓前,痛哭流涕,说着她的憋屈,她的伤心,她的决心。她拿起铁锹,一镐一镐撬开她丈夫的墓,将那块徽章和那把刀挖了出来。一针一线映孤灯,一人一影伤离别。母亲一针一线为这把刀更换刀柄上的布料,再用磨刀石将刀身上的锈迹抹去。看着母亲的身影,他心酸,但他知道既然选择了这条路就会愧对自己的母亲...
翌日,晨曦初晓,村民们都来送行,双手接下母亲递给他的刀和徽章,他看到了母亲满眼不舍,却仍面露微笑。
“去吧孩子,你的父亲是好样的,我希望你不要丢你父亲的脸,母亲我啊,会一直在这里等你回来。你小时候不是说,你想要一个自己的小池塘,养各种小鱼小虾吗,母亲我呢,就帮你实现你小时候的愿望,你一定要平平安安回来,看看母亲帮你做的小池塘好不好看...到了那边呢,多听话,多注意安全,多写写信回来,记得刷牙,天冷的时候告诉妈妈,给你寄点厚衣服去,记得...”
他的母亲,始终微笑,而他早就泣不成声。他明白,母亲啊,是不想在他走的时候哭,想让他记忆中,离别时最后一面的母亲是最美好的形象吧...

“各位乡亲们保重,我妈就拜托你们照顾了,如果过去有什么不周的地方还请担待,你们的恩情等我一点点偿还。”他郑重的向送行的相亲们说着,随即目光看向母亲,微笑着说道,“妈,我走了,等我回来孝敬您。”
这一年,他23,他的母亲53...
...
初秋的夜空,像一块黑色幕布,隐约看得见那一两颗忽明忽暗的星星,月牙儿似一把镰刀挂在空中。月光似无形的绳索,一头牵着他,将他的身形拉高,挺拔,而另一头却将远在家乡的母亲逐渐束缚的几近佝偻。
前两年,由于战事并不是特别紧张,母亲隔三差五还能收到他的来信,信上说,军营生活很好,战友们都很和善,最近接连打胜仗,等完全收复失地,他就可以回家了。他也收到了他母亲的回信,家里生活一切都好,村民都很照顾她,隔三差五就会收到米,肉,他的小池塘也快挖好了,占地一方,现在种着点小莲花,偶尔还有海鸟会躲在下面,等他回来,让他养他喜欢的小鱼,让他不用担心家里,注意安全。
然而,前线战事逐渐吃紧,邮差无法进入战事紧张的前线,他和他的母亲之间,彻底断开了联系。这一年,他30,他的母亲60...
...
时光荏苒,距离失联已经过去了10年之久。村长带人推开院落柴门时,他的母亲正跪在泥浆中补种着早春的莲藕。这段时间,村长已经不知是第几次来到孤湖了,春寒料峭的清晨,即便处于热带多火山地区,温度依旧很低。母亲用已经泡到褶皱的手掌扒开淤泥,小心翼翼的将藕种植入。
“何苦呢?”村长抬手按住了母亲正要放入湖心的竹篮,三十支新折的纸船哗啦啦的散落在水面,“你儿子走的那几年这个池塘才几仗宽,现在都快到海边了!”
他的母亲拨开挡住视线的白发,湖面倒映的天空正掠过迁徙的蓑羽鹤。最初那个方方正正的小池塘,早被数十年来的铁锹与泪滴凿成不规则的椭圆。雨季暴涨的水位会吞掉新栽的茭白,旱季龟裂的湖床又露出她埋的许愿瓶——每个瓶子里都装着没寄出的信,信纸边缘画着儿子离家那天的月牙...
“昨天勘探队来了,”村长拿着搪瓷杯喝着水,徐徐说道,“这个孤湖底掺杂着火山暗河,那边说要给咱迁到火山另一头的平原,你...”
啪!瓷杯在青石板上炸开,母亲推开村长抢回竹篮,篮中的纸船已经所剩无几,已经飘在湖面上的纸船连成一条红线,那是粘在纸船上晒干的红莲花瓣——在他七岁的时候,用偷藏的压岁钱给他的母亲买的发簪上一样的红莲花...
初春的风吹起他母亲的棉布衫,露出了腰间用红绳绑着的军用搪瓷缸——有次邮差喝醉说漏嘴,说前线战俘营暴动的那晚,雪地里留着这么个染血的杯子。自那天起,他的母亲把它牢牢的系在身上,红线箍紧的裂痕刚好拼出模模糊糊的“平安”二字。
“等湖面飘够九百九十九艘船,我的孩子就会踏着莲花茎回来...”母亲将剩下的三只小船轻轻推远...
劝说的村民们突然噤了声——晨雾散尽的湖心处,去年沉底的纸船正在上浮,信纸上晕染的字迹被水流冲刷成细长的墨痕——那分明是无数个“等”字在湖里生了根...
又过了数载,这是一个寻常,却又不寻常的清晨。薄雾里,母亲数到第九百九十九艘纸船沉入湖底时,火山灰突然在湖面聚成蓑羽鹤的形状。她解下搪瓷缸正要盛水,却捞起半枚嵌在钙化贝壳里的军徽——正是当年她亲手交给他儿子的那枚,属于她丈夫的那枚...
那一年,母亲离世...村民们将母亲的骨灰盒深深埋在池塘的中间,满足她等待儿子回来的心愿。
...
半年后,迁徙的车队驶过山道那日,村民们发现,一个不大不小的铁盒安静的躺在湖中心的莲叶中,盒内是厚厚一沓字迹陌生的信,每封落款处都印着带火药味的唇印。最后一页夹着半片染血的莲瓣,背面是儿子用那把刀尖刻的"妈,塘里的鱼该产卵了,莲子也该收了"。
这年他40,母亲69。
...
孤湖也就此永远的保留下来。 村民后来才明白"孤湖"名字的由来——他的母亲佝偻着脊背在湖岸犁出的沟壑,恰似个永远缺了左半边的"孤"字,地质图上的湖岸线逐年扭曲,像极了她望向星之塔方向时,被岁月逐渐压弯的腰...

如今每逢雨季,莲花盛开的时候,那些沉没的纸船便会在湖底排成归乡的箭头,而最深处的火山岩上,永远留着两双大小不等的足印:一双踩着未化的雪,一双沾着春天的泥...
(一天发两篇,一月开跑车,一年迈巴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