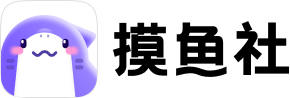盛夏的阳光照射在向日葵花田的金色浪潮之中,而在金色浪潮中隐藏着一栋窗户都被窗帘所遮挡住的破旧小木屋。
但是,木屋的内在并未如同外貌一般破败,也并没有如同窗帘遮挡窗子这样的行为一样的阴沉。相反,木屋内反而是充斥着阳光。因为其中摆满了向日葵的画作,以及关于阳光下的生活与自己所爱的事物。
而这些画的创作者正创作着新的画作,这幅画一样是充斥着阳光的成分,但是色调却较于房间内其它的画却显得异常阴沉。画中的阳光虽然照耀着画面底下的士兵,但是士兵含泪所望着的阳光所及之处却是一片死尸,而唯一活着的自己却仍然被战火的烟尘所笼罩,不由得让人感受到一种压抑感。
而此时创作者正画完无人问津的尸体倒在阴影之中的最后一笔,然后缓缓地在画中留下来了一首小诗:
我走过这
成排成列的尸体
在昨天的同样时间
他们还认为很安全罢
谁又能知道我们到底该去哪呢
这炽热的感觉
我不知道这灿烂的阳光还能照耀我多久
但我知道母亲会为死后得我不住的哭泣
“朵拉?这是怎么了,突然画起来这种风格的画来了。”我静静地看完了朵拉轻轻地绘完了整幅硝烟气十足的长篇画卷。至于我为什么知道她并不是突然起意而随便画的原因的话,如果一个人为了一幅画准备了好几天,然后将后面又好几天的时间投入到了这件事的话,肯定不会是临时起意了吧。还有在画这幅画的时候,我是真的为朵拉的身体感到担忧啊。她本身身体就差,还天天熬夜和饮食不规律。每次我看见她摇摇晃晃的身体都为她昏倒的可能性而担忧。
“没什么,只是完成我一直想画的类型罢了,哥哥。”朵拉伸展下了自己轻柔纤细的身段,将因为绘画而僵硬无比的手臂与胳膊放松放松。“在以前的世界,我就想试试画画这种悲伤绝望但是依旧有着些许希望的战场画了。嘿嘿。”我不由得拍了拍她的脑袋。“那也要注意下身体啊,别一天到晚都呆在这。看你画的那么起劲,我也不好去打扰你了。还有,这幅画真的有希望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呢。”
“笨哥哥,你看这。”朵拉踮起脚来敲了敲我的脑袋,随后将手指向了了那个唯一活着的战士的位置。我凑过去仔细看了看才发现他的脚边依然有着些许绿意。这在这片被炮弹所炸成焦土,被芥子气染成黄色的战场上这些许绿意毫不起眼,但是当你注意到它之后却显得异常显眼。“这可是向日葵的幼苗,它一定能长大成为这片战场未来的希望的。”
“不过你是说,你一直想试试这种画?”“对啊,但是我又不能出门。没见到过多少次焦土与战斗的痕迹,而现在我去魔女境界见到好多啦。”“是吗?”我不由得摸了摸自己的下巴。“那你要不要见识下真正的战场?正好西西借了我她的vr游戏机玩,我记得里面有个叫铁心四号的可以在田野打架的拟真世界游戏。你要不要试试?”“笨哥哥。”我又毫不迟疑地吃了一记来自朵拉的头槌。“不要在陪我的时候提起其它姐姐的名字好不好?”
“好好好,那么我们就试试?说不定,你还能找到关于你的绘画的不完美之处。”我边揉着被她头槌槌的有点发疼的心窝,边布置好了来自西勒诺斯的游戏机。随后将自己与她的游戏头盔都交了出去。“好呀,哥哥。我也想和你一起玩游戏。”
当我和她一同进入游戏世界的时候,她所绘出的那幅画却散发出来了光芒,让我们的旅途多许多变数。而发光的同时,从画中也传出来了轻缓磁性而绝望的歌声:
乌云向东边飘去
村庄在燃烧崩塌
鲜活的年轻生命在逝去
死亡的阴影将我们笼罩
它们侵蚀着整块土地
手里只剩下了沙子
眼中只剩下可怕的战争
很快我就会同其他人一样躺在冰冷的坟墓里吗?
而这一切,进入到了画中游戏世界的我们都将无从知晓了。
随着缓缓地进入了游戏的界面。我还没有睁开眼睛就听见了呼啸而来的炮弹声,而周围也传来了惊呼与咒骂。而我睁开了眼睛,才发现我身处于战壕之中。我抓紧时间将四肢撑在地面,而肚子却尽量别贴到地面上。然后我随后打量了下自己的打扮。蓝灰色军装,但是手臂上还套了个带着红色十字的袖章,自己还顶着个头盔。
“妈的,阿勒曼尼蛮子们又要冲上来了吗?”卧倒在我身边的士兵咒骂着。“每次都是这样,天天都是这样,真的是没完没了。”“医生!医生!”我感受到有人扯了扯我的手臂,我很快就意识到了我的袖章是医生的意思,因为其它士兵并没有这种标识。“这边……”
不过很快,我便听不清那个士兵的诉求了。因为,新的一轮炮击已经到了自己的身边。咻,boom!随后我只能听见一阵耳鸣了。
而我也发现我也没有必要再听清那个士兵的诉求了,因为此时他的脑袋已经不见了。而旁边那个咒骂的士兵也一样看见了,随后闭着眼睛又轻数了个数字:“98,好了,现在皮埃尔也走了。”而我还没从这种情况反应过来,就又从耳鸣中听见到了战场的鸣响。“医护兵!医护兵!医护兵!”这是新的哀嚎。
而我听到了这些哀嚎之后,身体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身体就如同完成任务般似得冲向了那个哀嚎之处。而当我冲到了这个地方之后,看见了大腿血流如注的年轻孩子。看着只有十六七岁吧。
“孩子,孩子。镇定下来,能告诉我现在你感觉怎么样了吗?”“痛痛痛。”而当我想治疗他的时候,本来毫无办法的脑子突然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然后我就如同看着动画一般地看着自己帮他完成了简单处理。但是很明显这片焦土不适合为他完成一切的处理。
“好吧,该死的。得把你拉去医护所才能救你了。”我一把把他背在了自己的背上,顺着内心的感觉弯腰奔向了后方。不知奔跑了多久,我才背着他回到了战地医院,而此时我也才又再看见了朵拉。她身着合身得体的白色护士裙,笑着对我打招呼我说:“哥哥,看来这次我们是主从paly呀。听这里的人说,你似乎是一个老是喜欢往战场跑的医生,而我是你最得力的助手护士。”“好了好了,这些话后面再说吧,先救这个孩子。”我连忙把那个少年放在了手术台上。
“嗯。哥哥,我明白的。”朵拉一改之前的调笑表情,认真的点了点头。随后,我们二人便打起来了配合。此时少年的面色已经开始从苍白变为红润,而我知道这并不是好转的表现,而是最后的回光返照。“别睡好么?坚持住,我们会救你的。”朵拉轻轻地呼唤着已经开始意识不清的少年,一脸紧张而认真地和我配合着治疗着少年。
而少年也最后被我们从鬼门关抢救了回来,幸运地只是失去了一条腿。而事后的少年,一直在宣传他是因为在死后看见了天使,是天使将他从死亡的深渊之中拉扯了出来。
而后面我又收到了一个伤员,这个伤员较于少年就倒霉多了,浑身焦黑像是被炽烤过一般。而最后很遗憾的,我们也没有将他抢救回来。而他焦黑的手中却还保护住了一条白金色的吊坠,我和朵拉好奇地打开了吊坠的盖子,果不其然地里面是装着他与自己妻子或者未婚妻的合影,为什么会知道是?当然是因为盖子上的刻印:“致我最爱的让,你最忠实的玛丽娜,愿全知全能的主能保佑你在战场平安。”而当我看见这句话与他的时候,这片战场就已经不再存在主了吧。
之后我也见过一位伤员,死状异常凄惨。当我给他擦干净,去找他的伤口。当我打开他的夹克,看到伤口的尺寸的时候,我就已经在怀疑他是否能活下来了。血和气泡从一个大洞里面冒出来。一块炮弹碎片先是从脊柱附近钻入,然后穿过他的左肩胛骨和肺,从他上半身右侧射了出去。看来他的内脏仅仅只是被他的制服固定住了。而朵拉并没有为此放弃,她依旧坚持着与我奋战于这位伤患之上,可是天使终究无法在无主之地起死回生。
我们就这样在这待了许多天,我与朵拉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其实主要是朵拉,她那纯白的头发与眼眸过于惹人注目了。而且在这个世界还有好处就是朵拉的疾病消失了,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医护工作之中。而她那纯白的身影加上甜美的声音以及认真的身段让整个师内都流传出来了坠落于无主之地的纯白天使的称号。
我们救治了数百伤员,也送走了多于伤员许多倍的死者。其中我也读到了一封信让我感触颇多:
你好,亲爱的朋友!问候你,也向你告别,因为我已不再活着。只有在我牺牲后,这封信才会被寄给你。但我能感觉到,这一天并不遥远。我不知道它在我的衣兜里还会放上多久,已经有点皱了,但迟早它会寄到你的手中,最后一次提醒你记住你的同学。
在这最后一封信件中,我有一种冲动,想跟你说上许多,许多许多。我想倾诉未尽希望的所有悲伤,向你传递我对这一未知死亡的恐惧。没错,亲爱的朋友,恐惧,我很害怕死后的情形。
我不知道自己会如何死去或死在何处,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阿勒曼尼人的机枪子弹击中,还是被一颗炸弹炸成碎片,或是被弹片打死,但每一种死法的可能性都令我惊恐不安。我已见过数以百计的人身亡。我也曾多次听见战友在临死前从喉咙里发出的惨呼,而就在不久前,我还兴高采烈地吃着跟他们从同一个桶里打出的饭菜。
我曾多次面对死亡。有一次,弹片把我头上的帽子击落。还有一次,子弹射穿了我的饭盒,汤漏了一地,结果让我饿了一顿。但过去我从未像现在这样害怕过。
看看你那里,春天来啦。这句话的九个字令我心神不宁。因为这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春季,这个春季我就二十岁了。二十岁,快是个成年人了。我死去时,大自然正向你展露笑颜,你的心跳伴随着满腔的喜悦,因为鸟儿的歌唱或潮湿的春风轻柔的爱抚……
这封信是我从他的手中找到的,下半部分还没有写完,因此我们再也不知道收信人将会是谁了。
而一些尸体在我们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活着,他们同样给了我们不少信件。有一位军官临死前将他写好的短信交给了我们:
复活节中,我的思绪经常自然而然地飘向你……我无法下定决心写那种刻意的告别信……你那里收藏了很多我写的长信,而且你对我非常了解,我也没有必要写一份“悲惨”的告别信……我知道,你会为我好好地抚养孩子们,我不必担心……
我们也见到了许多阴沉和懵神的士兵,我们的长官都说他们是胆小鬼和懦夫。不过据我的医疗知识所言,他们应该是弹震症的患者。
关于这种患者,我也曾见到过一个典型案例,那就是一个我在师部都听闻过的战斗英雄。他的品德和行为还有英勇程度都是毫无疑问的是第一梯队。
但他现在已经变成了战场行刑队枪口下的亡魂了,因为他当了逃兵。我所知的只是一个星期前,他亲眼看着自己几个朋友的脑浆飞溅到了自己的脸上。
我们不仅救治着友军,同样救治着俘虏。我们也曾救治过一个阿勒曼尼士兵,当时他被炮弹炸晕了过去,然后被俘。但是倒霉的他依旧挨上了数枚子弹以及炮弹片,不过他被我们从死神的怀抱中抢救了回来。而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师中居然还有活人会认识敌方的士兵。
“我认识他!嘿,汉斯!原来你也上战场了。我还记得你给我剃头的时候。我还给你修过篱笆呢。现在我们都做不成啰。”说这话的人是一个右手截肢的士兵。而他口中所言的汉斯同样也因为坏死而双手截肢了。“该死的战争,该死的你,该死的我。”
而我在刚进入这个世界所看见的那个默数人数的士兵同样没活过第三天。而他留下来的并没有什么感情深重的信件,也没有什么光荣与牺牲的语句。他只留下来了一个记录着他们连队战死士兵姓名与性格还有死因的笔记本。而我替他写下来了他自己的名字以及死因:让·艾顿龙格,死因:为了保护新兵。
我想如果他记住了别人,那我也应该要记住他。因此我也将笔记本留在了自己身上
而在尸体上我们发现的不仅单单只有死亡的痕迹,还有着生命。我和朵拉被一位来自罗刹的士兵赠予了来自他故乡的向日葵的种子。而他在临死前对我们的要求只是将他与故乡的花葬在一起。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和朵拉也在这个世界呆了数个月,而这段时间中战线也只是推进了一英里,正当我们已经习惯于与死亡作伴与死神作战的时候。那几粒种子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芽,开花了。而当鲜花盛开的时候,世界开始崩溃了,随着炮击与怒吼,像是某个人的噩梦开始苏醒一般崩溃了。首先崩溃的是大地,其次是坠落的天空。崩坏的大地吞噬着无人区的尸体,坠落的天空掉下无数的炮弹吞噬着活人的生命。我和朵拉也就因此而睁开了自己沉睡的眼睛。
窗帘已然不再透光,而这也代表着天色已黑。我们相顾着对方不知道说什么好。“哥哥,我想到该怎么改了。”朵拉想起来什么似得用拳头敲了下自己的掌心而望向了画。但是她呆住了,因为画中的士兵的眼睛已然不再流泪,而脚下的绿芽已然开花。围绕着向日葵的他所面对的依然是死亡的阴影,但是阳光却已然驱散了硝烟。
“我想,我应该不需要改了吧。”朵拉轻轻地摸索着这幅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