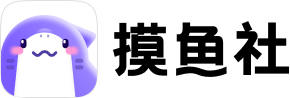【幸存者联盟】
3
哥的理论我绝对赞同,但是他的混出来的经过实在令人不齿,真不想说,怪丢人的。炒作嘛!有本事凭实力打出码头来,有本事像我一样,我这样的才叫奋斗哩!
那次从家里再回到学校,我整个人就变了。有种的气息由里而外地散发着,谁见了不害怕呀?——什么,说说我哥?嗨,不值一提,简直就是给出来混的人丢脸,误打误撞,纯属炒作!他就在宿舍睡午觉呢,宿舍楼那边是几个水泥兵乓球桌,中午总有人在那边吵吵嚷嚷地打球,整幢楼的人都不能好好休息,受害久矣。这一天我哥穿着三角裤靸着鞋,跳到一块水泥墩上,扬着指头吼了那么几句。那些打球的抬头看了看,没人回话,等我哥回到宿舍,打球的一个不剩全走了,后来才知道,其中两个还是体育老师。这就了不得,个个都说我哥有种,没几天功夫我哥就成了他们高中公认的大混混,连对面体校的人都主动过来结交了——多可笑,不是所有人的革命生涯都如你想象的那么严肃,投机取巧,炒作上位的大有人在。接下来该说我了吧?
自从有了种,我就更嚣张了。夏天自然只穿一件短袖衬衫,扣子自然一个不系。春、秋我只穿一件外套,里面真空,非但真空,拉链从来不拉。冬天只穿一件棉袄,没有贴身内衣没有毛衣,自然也是敞开的。一年四季,我永远敞着胸,露着乳。有种就是好,什么都不怕,冷也不怕。
当然,如果没有实质性的操作,只穿衣不系扣子,顶多是个脑残,而我不只是脑残那么简单,我还有种。我有种并不只是体现在我走路时永远昂着头目不斜视,口水迎着风吐出去,再让风吹回到脸上,还体现在我决定向学校里每一个稍微混得爽一点的人发出挑战。
第一个被我挑战的是五班的“老虫”。老虫的跟班打过我,老虫的跟班多嚣张,就因为我看了他一眼,他就跳起来打我,还让我道歉。我道歉了,既不觉得丢人,也不觉得委屈,我认为老虫的跟班算是真正的流氓,被真正的流氓打一顿,那还有什么好说的。何止不丢人,简直还有些光荣!现在我有种了,照说该找老虫的跟班报复才是,哈,偏不。在挑战自我这种大义面前,纠结于个人恩怨显得格局有点低了。我无视老虫的跟班,直接向老虫本尊发出挑战。
那又是一个无聊透顶的晚自习,我把物理试卷倒着看,倒着写,玩得正起劲时,忽然听见窗外有人压着嗓子低低地喊我的名字,我抬头看去,一个不认识的小瘪三隔着窗户的铁栏栅站在外面走廊上,教室里漏出的灯光打在他脸凑上前凸出来的部分,鬼里鬼气的。我刚走出教室,下自习的铃声就响了,可见他是掐着点来的。鉴于我小有名气且十分有种,我眯起眼睛瞪着他,用尽可能不屑的语气问:“搞什么卵?”小瘪三向我走来,越来走近,我看清了整张脸,认出这小瘪三正是那个打过我的老虫的跟班。
我的思想在一瞬间凝固,血液也凝固,空气也凝固,只有老虫的跟班在继续向我走来,他在离出拳刚好能打到我那么远的距离停下。我脑子里升腾起一百种击垮他的打法。我的思想跳动起来,我的血液澎湃起来,就连空气,也充满了杀气,躁动起来。我要先将他的脑袋往墙上撞,嘭地一声闷响;再将他的脑袋往窗户玻璃上撞,啪一声脆响,紧接着是玻璃着地哗啦声和女生们的尖叫声。小肚子给一膝盖,下巴来一记上勾拳,这时他基本就醉了。我再有条不紊地一手揪住他的肩头,一手啪啪啪啪地打耳光。老师肯定一时来不了,走廊会挤满了人,交通会完全瘫痪。群情会激奋,欢声震着天。